
2023.5 精神食粮
书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疼痛部》
故事松散,甚至有些乏善可陈,但写出了深具层次的被剥夺感。“疼痛部”是海牙的一家 SM Club,对流亡的人而言,疼痛是无言的,无用的,却唯一真实的证人。被驱逐失去故国,继而失去家,语言分叉成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马其顿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对时间地点的感知也被永久地改变——战争永不结束,也永远回不去日常。
流亡者常常觉得铭记是自己的责任。而如邻座的建筑师所言,忘记是轻松快乐的,立一只替罪羊,让其他人替我们受苦和铭记。如果有人想要遗忘,应该以责任之名逼迫他们铭记吗?遗忘对历史不公,何况“时间不治愈伤痕,时间制造伤痕”,但就像鲍迪耶掉入深井,找到记忆那一瞬也一样通向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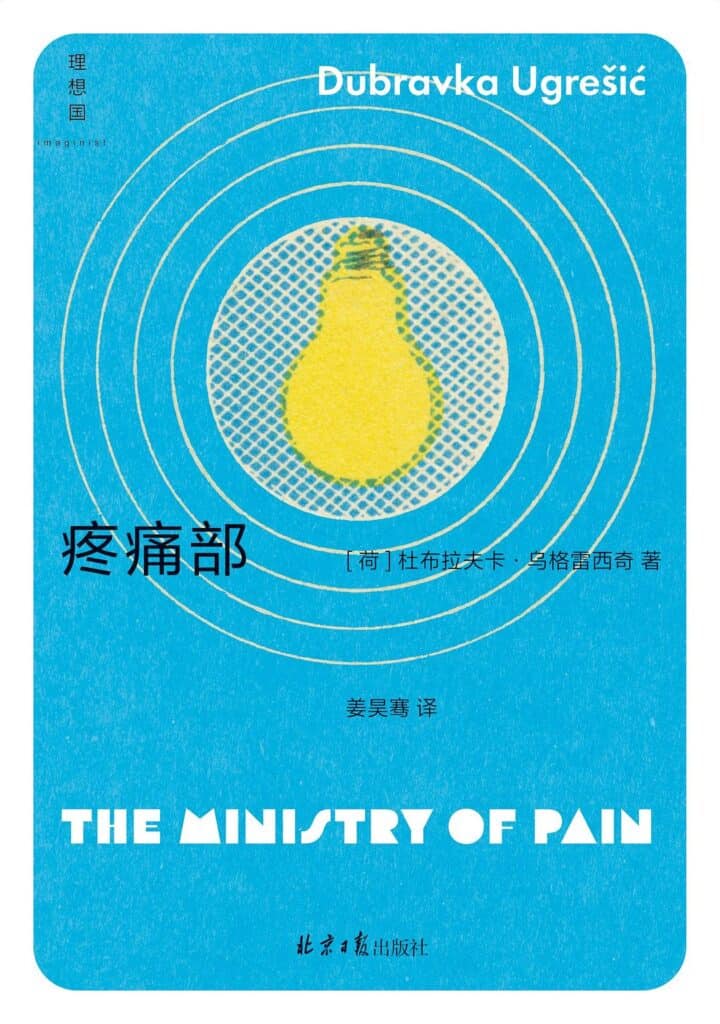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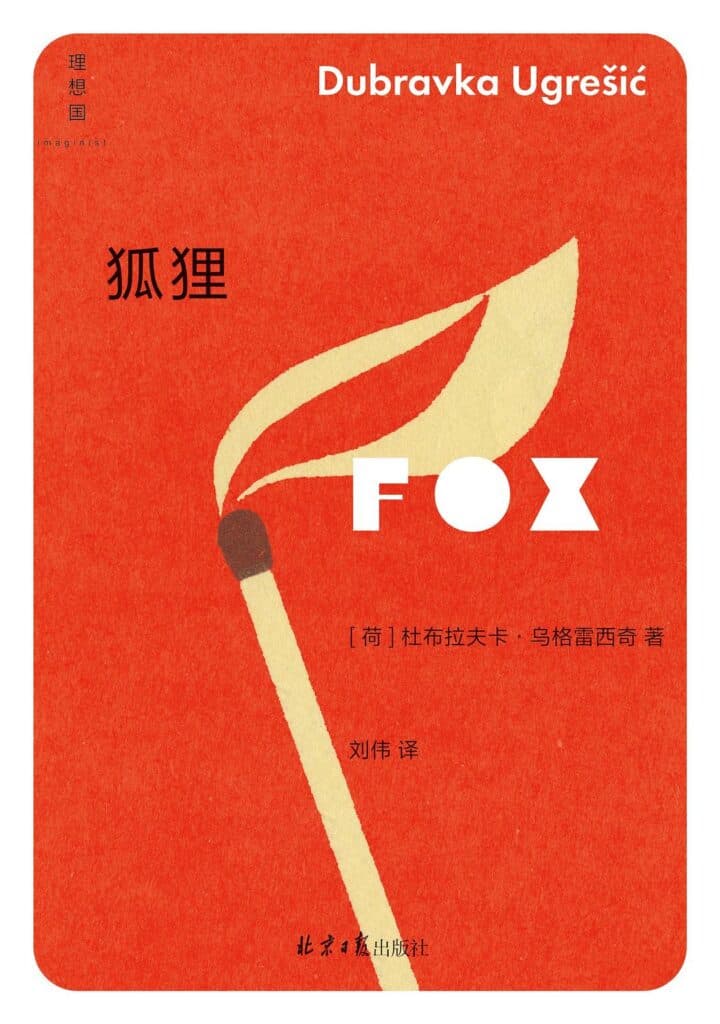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狐狸》
重新翻了一遍中译本,还是最喜欢第一章,结构坚实,环环相扣,又如同整本书的缩影,与《微暗的火》一样,脚注也能叙事,与正文叙述者可以不是同一人。“我”在莫斯科及母亲在小火车站、索菲亚的简短自传、《痴人之爱》、田垣的小说、皮利尼亚克《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都是不同层级的文本,每一层都是创作,都是狐狸,书外的读者无法确认这其中究竟含有几重背叛。
皮利尼亚克说狐狸是作家的图腾,但随着小说展开,你会发现这巧妙编织、密密层层的文本也是狐狸(用近期多次听到的说法——“文学是巧言令色”),甚至人的身上也可能附着无数版本看不见的文本。又有可能如纳博科夫所说,人类生命不过是晦涩难懂而未完成的杰作脚注罢了。狐狸边缘弱势却也狡黠,无论生死都能搬出诡计甚至魔法,脚注不懈而绝望挣扎着的生命,也能对抗时间和死亡。
伊沃·安德里奇《德里纳河上的桥》
德里纳河上的桥,“永恒存在于潜意识中的神圣遗产”,16 世纪由一位出身此地的大宰相捐赠修建,历经几百年后在一战战火中被炸断。安德里奇的笔法像民间传说,几百年的时间跨度,历史转向的时刻,全知视角及有限的内心描写,按末尾授奖词的说法,他“使现代洞察力与《一千零一夜》的宿命观结合在一起”。小镇靠近塞尔维亚边境,不同民族和信仰杂糅,安德里奇笔下有这些群体统治与被统治、迫害与被迫害的更迭交错,平凡居民无法被满足的欲望,得不到的美好生活,永远虚空的梦想,以及被历史和命运漫不经心地拨向深渊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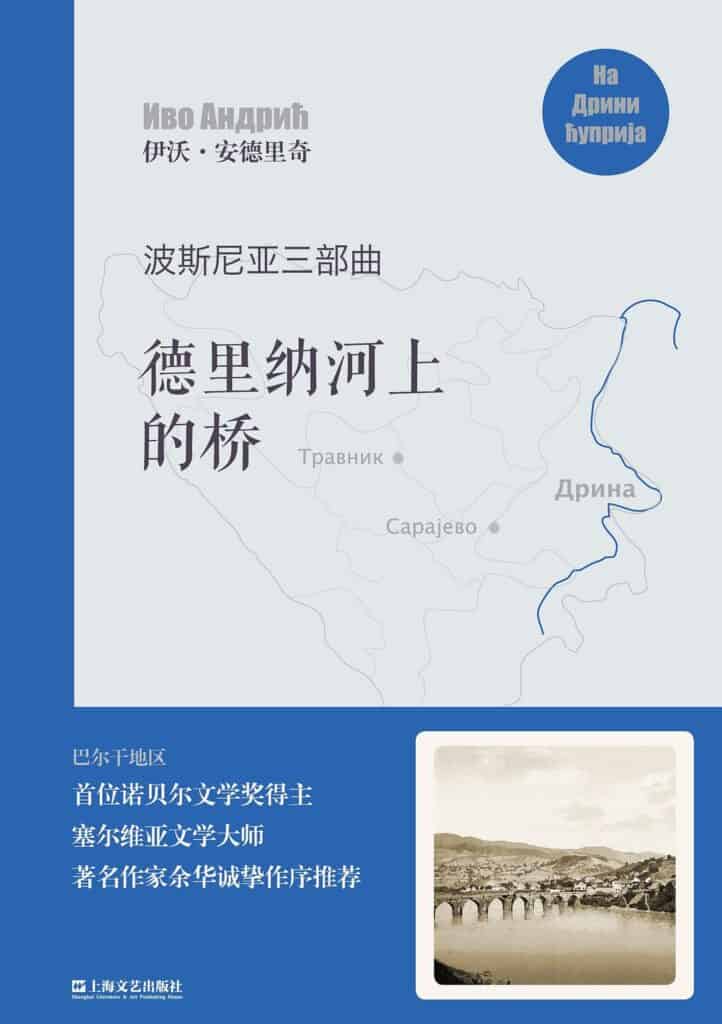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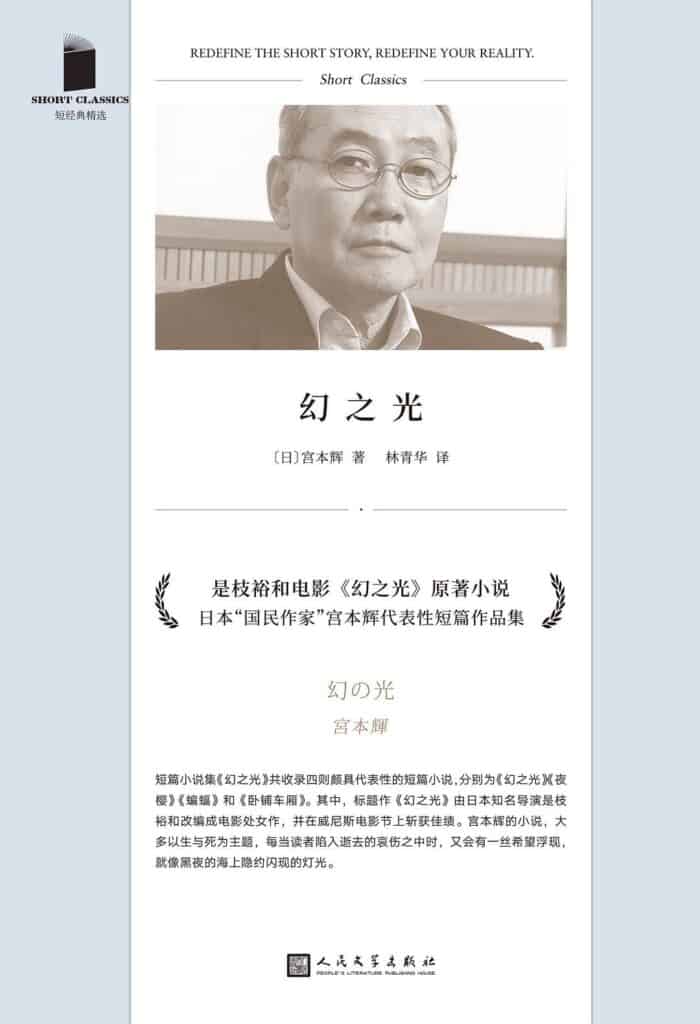
宫本辉《幻之光》
宫本辉写的是气息、氛围、以太、暗物质,文字上方那一团看不见的东西。每每人物带着丧失的哀恸撑过一段人生,行至篇末终于迎来醍醐灌顶的时刻,关于这醍醐是什么,读者也许能勉力一猜,但宫本辉欲语还休,猜测就也始终是猜测。 他规规矩矩,形式和语言都没什么花活,却知道把什么与什么并置,怎样一笔带过暗示。我好像很久没读平民视角的小说了,他自己也有颠沛流离的童年,写得自然平实却有四两拨千斤的灵巧。他的人物都有不同寻常的敏锐和洞察,却显然拥有各不一样的灵魂。
These Possible Lives by Fleur Jaeggy
4.5,Fleur Jaeggy 的语言轻盈灵动,很多句子非常惊艳,让我想起李斯佩克朵,出了英译的几本书也跟李斯佩克朵一样都是百页左右的薄本。三篇人物小传分别写 Thomas De Quincy、John Keats 和 Marcel Schwob(她是 TDQ 和 MS 的译者),早慧早熟才华惊人,却困于病痛、贫困、药物或早逝。
她以一种独特而新鲜的方式接近这些作家:
Thomas surprised his shoes and went skating down the street.
Keats came across a being with a strange light in its eyes, a rumpled archangel – he recognized Colerid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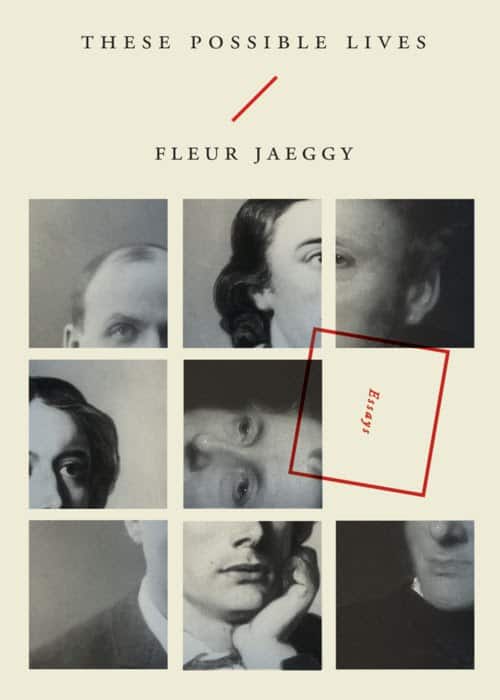

The Water Statues by Fleur Jaeggy
谁能想到罗伯-格里耶风的小说如今读来反而显得挺古典,Jaeggy 飘忽、摇荡、沉溺,人物总望向远处,一直放空,可同时又能感到她全副身心的投入。Beeklam 喜欢沉默的同伴和沉默的雕塑,Jaeggy 也喜欢沉默的同伴(她曾盛赞巴赫曼的沉默)。雕塑——凝固的时间和面容,偶像——在水中漂流,撞上地下室的墙,灵魂也如 Flying Dutchman 在七海永航。
阿兰·罗伯-格里耶《去年在马里安巴》
读完 The Water Statues 之后就去读了格里耶。我可能遇到了打开格里耶的最佳时机,现在他读起来有种纯粹,人物极其有限,时空和已经足够贫瘠的情节被打碎,连细节都很少。《去年在马里安巴》与其说是剧本不如说是脚本,一大乐趣来自文本和影像的对照与对话,剧本使读者注意到镜头、姿势、道具、表情和配乐的考量,以及有时仅仅“看上去有所考量”。如果格里耶的小说里有什么能吸引读者,也许就是可传达与不可传达间的模糊性。格里耶遇上阿伦·雷奈对剧作家和观众都是幸事。生命不是按照均质的线性时间在过,记忆的样貌也更像是一块块零星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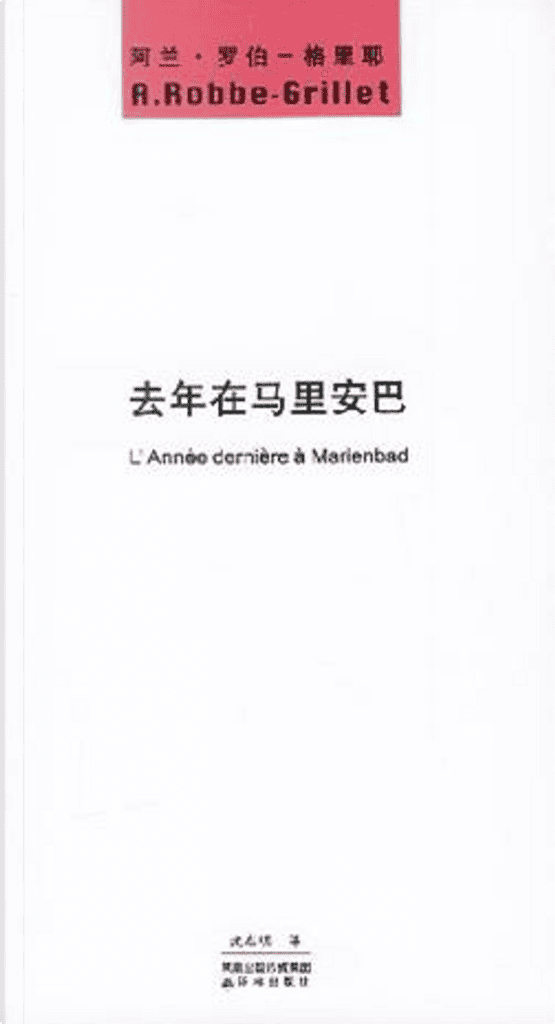

伊塔洛·卡尔维诺《观察者》
卡尔维诺少被提起的小说,也是去年才有中译本,最初出版于 1963 年。与在魔法世界中跳跃的卡尔维诺非常不同,这个中篇体现的是 19 世纪小说的传统,纯然的现实主义,节奏紧凑,讲述一个年轻人阿梅里戈在投票站科托伦戈做监督员的一天。科托伦戈是一个天主教福利机构,里面有大量神智不清、生活无法自理的病人,难以确定投票是出于真实、自由的意愿还是被党派利用作为自己稳定的票仓。卡尔维诺探讨了民主覆盖的范围(是所有人吗?),自由意志,公民权利的门槛,政治理念与生活实践。
促使我去读这篇小说的是伊恩·麦克尤恩聊它的一期播客,主播 David Runciman 是剑桥的政治学教授,此前与 Ben Thompson 共同主持 Talking Politics,Past Present Future 是他的新播客,与麦克尤恩的谈话是第一期节目。两人聚焦卡尔维诺关心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应该被赋予投票权利,如何界定“清醒的精神状态”,高龄老人呢,孩子呢?卡尔维诺本人也经历了政治立场的转变,从 40 年代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到 1957 年因苏联入侵匈牙利而退党。阿梅里戈在投票站经历了民主理想和程序正义的幻灭,这大概也暗示了卡尔维诺政治理想的幻灭。
对于读中译本的读者来说,主角阿梅里戈·奥尔梅亚的名字会掩盖它的拉丁字母 Amerigo Ormea 所做的暗示与调侃——America,麦克尤恩说卡尔维诺的名字伊塔洛(Italo)就是“意大利的”的意思,而他出生于哈瓦那。
张琴《长夜的独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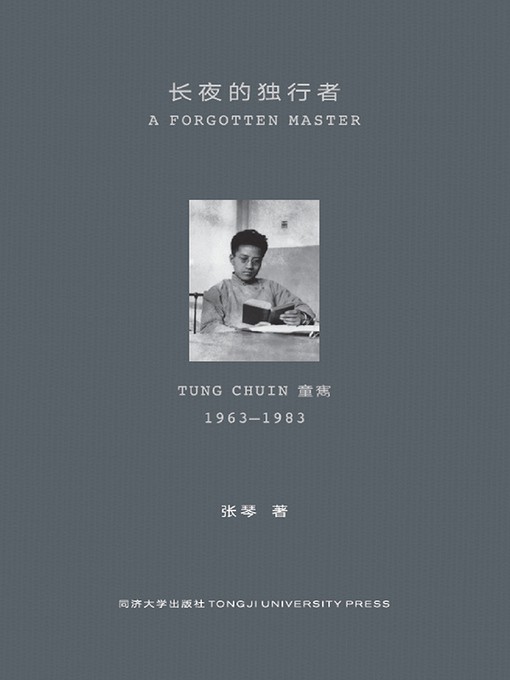
上个月看了童寯的纪念展,顺带读了这本小传,作者张琴是童寯之孙童明的妻子,有许多家人视角下生活经历的描述,一个知识分子看着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在抄家、交代材料与友人接连受害故去时,他又是怎样妥协与尝试做最后守护的。
这期节目是在南京的童寯故居录制的,嘉宾是前文提到的童明与他的好友董豫赣,坐在童寯故居回忆旧时生活情景自然令人动容,也解释了「东南园墅」「西行画录」两展的策展思路。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董老师谈到园林的方法论、园林的现代性时讲的一段话:
现代性是什么?我理解的现代性来源于西方,其实就是人文主义开始思考自我。不是你告诉我、神告诉我应该怎么生活,来世应该永恒或什么。所以它不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它是在任何时代,只要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是现代。那现代建筑是什么?现代建筑意味着你不能再拿神学的教堂的价值来判断建筑学的优劣。当西方用(某个标准判断)美丑,那你如何去给学生打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你给他90,给他85。然后如果你说我拿永恒或者什么东西,它属于教堂,我们现在也不会信,哪怕装模作样我们也不可能真的信。
反过来就是中国它积累了一堆的东西,非常的古老,其实古老的正好是谢灵运他们那个「山水方滋」的时代。首先写诗,你不再像汉赋那样排比,那叫铺陈,你要夸皇帝的东西有多么雄伟,你可以用一堆排比句。刘勰总结山水诗的写法,显然开始出现了一个叫对仗对偶的东西,因为它不是叙事了,叙事你需要因果关系,对吧?但如何把山水内自然的意象,就像没有人告诉你一样,用字呈现出自然本质,就不应该是因果关系,而是同时并置。所以文学已经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方法,而且我相信就像哥特教堂一样,没有一种叫教堂的方法,而是大艺术的方法,这个方法是通用的。几何代表的永恒,既属于绘画也属于雕塑,甚至属于当时的音乐,也属于他们的建筑空间的那些做法。与此同时中国囊括了所有艺术的山水,它的方法一定是可以做建筑,可以做园林,可以做——我现在特别不习惯用景观这个词,那山水你去面对它——我在这里就能找到关系这么一个词。
播客
鲁豫主持的这季节目里只听了访谈张怡微这一期,她的成长经历、台湾交换和读博的经历都很精彩,但此时我最想分享的东西却有关韩国文学和小说的世俗:
韩国作家的作品里有不被祝福的恐惧、资源被掠夺的恐惧,贫穷,具体生活的困难,韩国文学写呕吐、厌食症,是身体性的对社会规训的反抗和社会问题的展演。如果停留在表象描写,就只是女性的社会性表达,可贵的是金爱烂的小说里有精神性的追求,住在漏水的地下室里还有一架钢琴,这种精神性的东西并非文学女性专有。这些好的女作家提醒我们身边的女孩子并不糊涂,她们可能没有那么勇敢和强悍面对自己不完美的生活,但她们一定有精神性的出口,你不要打扰她,你也打扰不了她,她总有一台钢琴在心里。
写小说是俗事,创造的乐趣来源于无常、命运、不确定性给我们以生活的教训,不在于思考宇宙是怎么运作的,制度、政治不是小说的忧虑,是诗和散文的忧虑。小说的忧虑更世俗,更接近情感,更接近人的欲望,人复杂的感情。小市民的软弱、自私、贪婪,我也怒其不争,但更多的时候有一些朴素的感情,是我很留恋、很难爬出来的,也是给了我文学的一生很重要的养料。
以文学读者为核心受众的杂志如何触及更多人?这方面《聯合文學》做得非常好,对想要扩展受众的小众领域的创作者很有启发。总编辑王聰威谈及杂志的改版,比如换成更大的开本和彩图。另外主题上也有所扩充:作家喜欢的衣服、咖啡、电影和艺术去的地方、做的事情,改编电影和动画,大众小说,这些都可以变成文学杂志的内容。《聯合文學》认为文学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可以把文学当作一种衡量尺度,去衡量世界所有的样貌。
如果哪个月我没有推荐昨日之海,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昨日之海没更新,二是“推荐”两个字我已经说倦了。
这一期的主题春天是塞巴尔德式的、私人的、间接而隐约的指涉,依然动人。春天是反抗的时刻,是觉醒的时刻,是面对《洛丽塔》的读者的成长,春天是被遗忘、被尘封的东西逐渐复苏的过程,但不能通过遗忘来和解,记住过去才有可能有未来。春天是春雪,《丰饶之海》的第一本,春天是平淡、寻常却同样纤美的紫花地丁。
喜欢杜拉斯的读者不能避开更外围的这个做记者、写专栏,谈政治历史和社会话题的杜拉斯,她的硬朗、骄傲,甚至令人讨厌的自大都是杜拉斯自身的政治性。
“杜拉斯有一种特殊的抒情能力,把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缺点——对钱和肉欲的赤裸追求——变成魅力。在杜拉斯的世界中,钻石是一种带有性挑逗意味的装饰物,也是一种权力的东西。这么庸俗而商品化的东西,在杜拉斯那里会散发出一种琥珀的味道。这种对钱毫无保留的描写在观众和读者心中就变成了爱,变成一种抒情。”她对世界重新发号施令,重新定义和命名,让一切规则重新来过。
书的价值:纸书,翻译与出版业(聊到生气) | Vol.018
我的朋友梁福歇和他的朋友们做的播客,这集聊书、封面、翻译和出版,从读者角度看书封设计、图书定价、正版盗版的问题。行业有行业痼疾,读者也需要有读者的 conscience.
最后还讨论了埃尔诺 Mémoire de fille 中译本《一个女孩的记忆》的糟糕翻译,展示了书名翻译如何影响理解,正文翻译如何影响情感与结构。也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 Mémoire de fille 是化用自波伏瓦的 Mémoire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
推荐梁福歇聊埃尔诺的两集节目,日间散步和西夏酒馆,以及上月推荐过的昨日之海的埃尔诺节目。
任宁上次聊播客也许还是窄播时代系列,那时候还聚焦在媒介本身的生产、渠道分发和客户端之类的问题上,现在有了一些用户基数,也不是只有爱好播客的人会听播客了,其他有不同信息需求的用户也慢慢多了起来。小红书上推荐播客经常见到的标签就是#打破信息差,但事实上播客的功用远不止提供信息,或学习知识,或个人成长这样狭窄。
小众的内容有它的好处,一是容易请到圈内有影响力的人,二是这么垂直的受众也并没有多少选择。播客能够给一些情感陪伴(并不局限于音频媒介),即使在收音和剪辑上还比较粗糙,但是这种粗糙而热情的感觉是很珍贵的。举例“禁止攀岩”,即使一辈子都不会去这个攀岩点,单纯很享受听这么一群人聊攀岩的经历,遇到的事情和由此生发的想法。
伍尔夫较少被提起的一部作品,篇幅不长,但优美深刻。主播早川提出人和动物不能相互理解,却能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而伍尔夫想要揭示的正是不以相互理解为基础和前提的亲密关系的可能性。他谈到 Donna Haraway,她定义了一种非具身性的“看和回看”的关系,不以互相理解为基础,而是目光的交汇,期待与对期待的回应。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美好的时刻也往往不是智识上的交流或理解,而是没什么意义的对话和互动,在这些交互之间体会到了共鸣、亲密、陪伴和依赖。
有关墨西哥灰狼(Mexican gray wolves)的有趣故事,展现了美国环境观念的转变。六七十年代的西南部农场主对墨西哥灰狼深恶痛绝,因为它们会伤害牲畜的幼崽,特别是最具经济价值的小母牛,因此这个亚种在西南部被赶尽杀绝。后来随着环保意识的深入,墨西哥灰狼从被猎捕对象转向了被保护对象,而一位当年最厉害的猎狼高手变成了为扩增基因多样性而捕狼育种的人。
培育出的小狼放归野外也遇到了问题,由于长大了会失去了野外生存的能力,必须在很小的时候就放到刚生育完的母狼巢穴里,由母狼养大直至在野外独立生存。
当事人自己的讲述和互动比报道更生动,也完全不同。这期节目展现了各种意识形态、各种主义难以覆盖、无法解决的,具体的人和生活的问题。拍摄与被拍摄,权力的上下位,作为导演的知识分子与没受过高等教育还混过风月场的女人,都只是两个鲜活的人的侧面,真实的相处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这些。爱情和婚姻可以是角力,但出招与拆招没有什么现成的武功宝典分类和总结,说到底什么是重要的,跟人相处体验如何,快乐还是压抑,每个人只能自己亲历过,也只能决定和评价自己的选择。
长文
What an Ontological Anthropology Might Mean
为读《森林如何思考》做的准备工作,文章和播客给不具备相关哲学或符号学基础的读者/听众,用相对平易近人的语言解释了这本书的目的和主要观点。除此之外播客还有创作背景相关的介绍。作者 Eduardo Kohn 写道,
所有好的人类学都是本体论的,因为它向我们开启了不同种类的现实。
相反,我试图用在思考的森林与鲁纳思维进行一种接触,这样,这种森林的思考方式(它不再是人类的,因此不仅仅是鲁纳或我的)可以透过我们思考它自己,重塑我们,使我们变得不同。
虽然把文章放在这里,但我更推荐作者 A.O.Scott 朗读的音频版,在正文开始之前有4分多钟的作者的写作背景简介。从文中可以看出马丁·艾米斯对 Scott 巨大的影响,从青少年到现在,他一直存在于 Scott 的阅读生涯中。Scott 对艾米斯怀有巨大的感情,给了这篇一个出自《哈姆雷特》的题名,甚至他对贝娄和纳博科夫的赞赏都部分来自艾米斯的风格和评论文章。这种批评家对作家的爱意很不常见,却十分动人。音频版把这种动人的距离又拉近了三分,听起来哀痛又亲密,Scott 印象中的艾米斯不会变老,永远停留在三四十岁的类似摇滚偶像的形象,但他突然之间就不再年轻了,失去了作家睿智灿烂的老年,变成了永恒。
As is often the case when we lose writers, it may take a while to find him again.
The liberal complacency of Martin Amis
Terry Eagleton 相比之下就不太客气,他对艾米斯和他的小团体一直不怎么感冒,认为他们对当代文化的批评是从身处其中的一个特权地位出发,他认可艾米斯的文学才能,但也不认为他的小说成就有多么高(那个团体中他最欣赏的是 Salman Rushdie)。他批评艾米斯口不择言,从未向自己冒犯过的人道歉。但尽管如此,艾米斯过早的离世对文学来说还是一个损失。
Fleur Jaeggy Thinks Nothing of Herself
因为对 Jaeggy 感兴趣,找了她的访谈来看,Fleur Jaeggy 是一位隐居的作家,极少接受采访,因此纽约客这篇很珍稀。读完会发现她是极有个性的作家,她似乎没有什么表达欲,喜欢沉默,也喜欢沉默的伙伴,对于在场的其他人有逃离的冲动。谈到写作,她说I look outside. I look inside me. And nothing comes out. For months, sometimes even for years. The more time passes, the more I think I have no existence.
谈到 The Water Statues 中 Beeklam 与男佣 Victor 的友谊,她说 I often think there is a bit of servitude in everything. Even in the time that passes when one looks out the window. And, naturally, in memories. The more time passes, the more I think I have nothing to say.
What Susan Sontag Wanted for Women
Merve Emre 为 Susan Sontag 的新文集 On Women 写的序。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把女性相关的话题和死亡放在一起,仿佛这是一种自我否定甚至自我毁灭的力量。
她在1974年的日记中写道:”有一天,像我经常做的那样,思考我自己的死亡,我有一个发现。”我意识到,我的思考方式到现在为止既太抽象又太具体。太抽象了:死亡。太过具体:我。因为有一个中间词,既抽象又具体:女人。我是一个女人。由此,一个全新的死亡宇宙在我眼前升起。”
死亡的幽灵促使她重新考虑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考虑孤独的女性和女性作为一个历史类别之间的关系。她这样做的风格比她早期文章的张扬、好斗之美更加克制,仿佛把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需要她在某种程度上抹去她的特殊自我。
Magda Szabó and the Cost of Censorship
作者 Charlie Lee 显然非常了解萨博的作品,借着 The Fawn 出了新的英译本的机会,梳理了萨博创作的脉络。
但是,萨博想展示的不是人们熟悉的异见艺术家反抗国家的画面,而是不同的东西——沉默可以扭曲和毁坏生活的方式。
然而,这本书的真正主题不是审查制度的沉默,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沉默,是亲密关系的失败,使朋友和恋人漂泊不定。萨博将这种沉默理解为一种流放,在她的小说中,她研究了这种流放的影响,与他人的疏远也会使人们对自己感到陌生。
乐评人、书评人 Ted Gioia 第一次在 newsletter 上梳理自己的阅读史,此前只知道他精于音乐领域,阅读广泛,并不知道这样如饥似渴。他的阅读建议是越年轻越应该读经典老书,越年长可以读读新书。如果觉得对某个主题缺乏了解,他会集中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大量阅读。
他还谈及大量阅读给他带来的职业机会,以及由此结交了新的朋友。
一个挺有趣的短篇,把黑色星期五写成一个僵尸围城般血腥的节日,零点的厮杀过后,商场遍地都是尸体。叙述者是一个服装店的店员,ta 和同事的工作任务是帮顾客找到需要的衣服,避免被顾客杀掉,及清理尸体。
Photo by Trnava University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