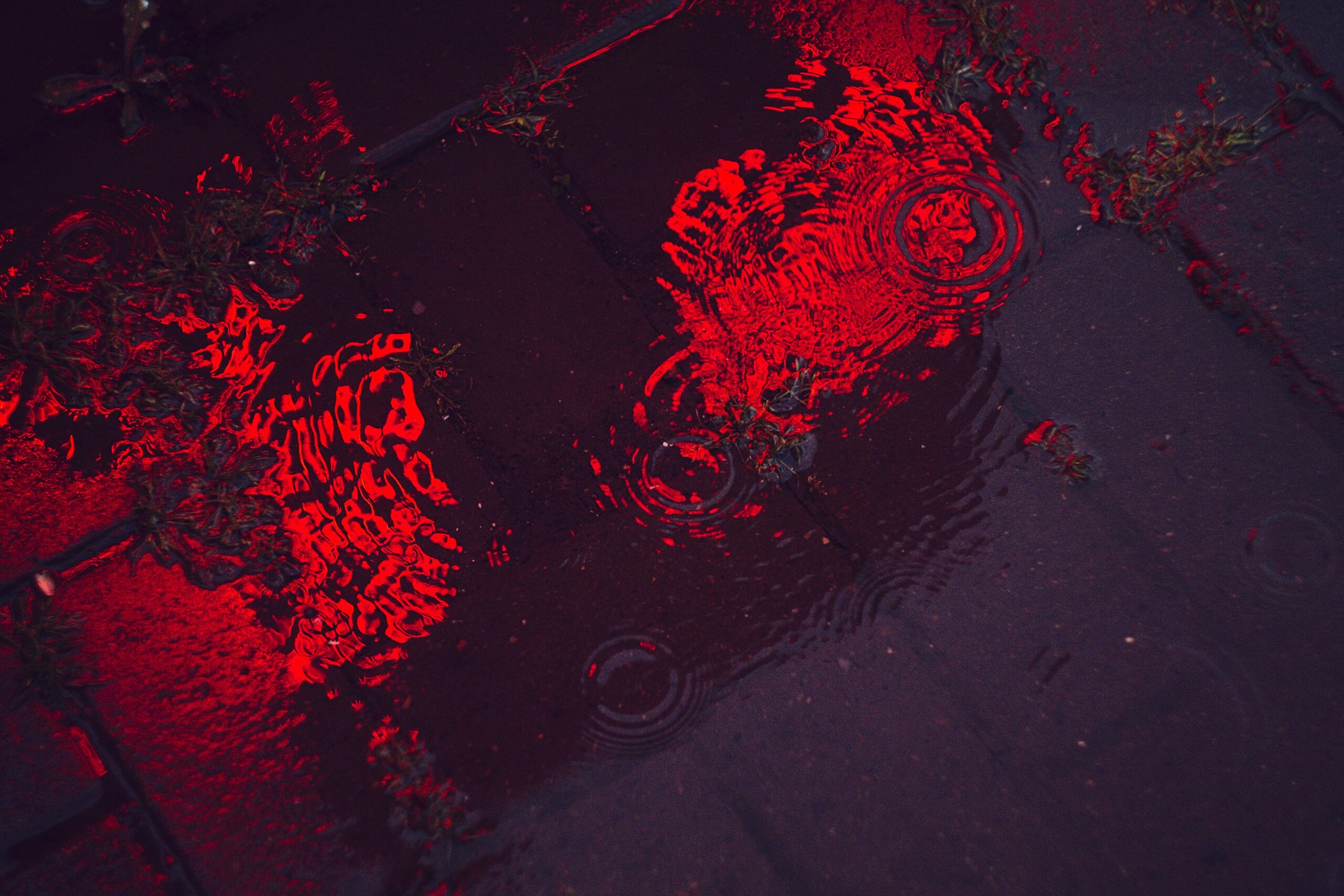
性、恐惧和屠刀
马库斯·梅斯纳,犹太屠夫的儿子,为了逃离父亲病态的控制而转学离家,他也同时逃离了年轻生命中全部的好运气,厄运从此开始。
主角马库斯父系一支几乎都做犹太屠宰生意,屠杀、切肉刀、鲜血、家禽牲畜在文中反复出现。《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也有一节专门描写机械化的屠宰工厂,吊钩和履带上的无数牲畜迎向被屠杀血流满地的最终命运。《广场》以批量的屠杀隐喻成为系统工具和零件却无从反抗的现代人类,而《愤怒》的鲜血和屠刀则承载得更多,既与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场遥相呼应,又暗指马库斯拼命想抓住主体性、坚持做自己,但还是与任人宰割的牲畜无异的结局。父亲的控制与室友的轻慢使他神经紧绷,来自大学保守价值的训导试图把他压进符合社会期望的模具,再加上他一贯以拿全A、做律师满足家庭期待为目标,重重压力下,他只能走向晦暗的终局。
根据犹太律法,洁净可食用的动物一定要一刀了结再经放血而死,奥丽维娅曾用剃刀割开手腕企图自杀,如果她成功了,就以符合拉比律法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屠杀。以温斯堡学院为代表的传统价值,了无生气的操行规范,以及性解放运动到来之前,以美德之名施于女性身上的种种枷锁,可能毁了奥丽维娅,她身在其中的环境——家庭的和社会的,以各自的律法屠杀了她。地名“温斯堡”也许取自舍伍德·安德森著名的《俄亥俄,温斯堡》(Winesburg, Ohio,又译《小城畸人》),正如罗斯隐约暗示的,这是窒息、怀疑与幻灭之地。
罗斯的作品中,性是最显眼的元素之一,彼得·沃森在《虚无时代》中写道,“大尺度的情色是罗斯的标签,是他笔下众多角色摆脱困境的方法”。但《愤怒》的主角马库斯无法被性拯救,一次期待之外的愉悦甚至标志着他一连串噩梦的开始。他与奥丽维娅第一次约会,经历了对方主动的亲密之举后反应是怀疑人生(长达三页纸)。这当然和他循规蹈矩的纯真有关,但在这里性不再是解决人生怀疑、摆脱困境的方案,正如对萨巴斯和祖克曼而言;反而是引发疑虑、踏入困境的开始。信奉“人臭翻天”信条的弗鲁塞,闯进马库斯的房间在他的每件私人物品上都沾满精液,这是报复与占有欲,以及可能变形的、病态的情感(尽管弗鲁塞的行为和动机都来自推测)。与之相对照,在panty raid里男学生侵入女生宿舍楼,用女式内裤自慰后把满是精液的内裤扔出窗外,则是被压抑太久以错误的方式爆发的欲望,传统、规训、道德在力比多的力量面前瞬间溃败,并最终彻底击溃了保持多年的规范。性欲,或者说广义的欲望,在罗斯看来是罪恶的快乐,生命力的表达,用沃森的话说是“颠倒式的生活的强度”,是愚蠢世界中唯一有意义的事。
在罗素眼中,“宗教首先并主要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对神秘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和厄运、人生意义的不可解释,信仰一套成熟建构并运行多年、承诺来世美好生活的神话系统是有利可图也便捷省事的方法。马库斯父亲的转变也恰恰是源于恐惧,社会变化对他并不有利,他恐惧生意变坏、境况变糟,刚长大成人的儿子不再优异和顺从。如果是(性)欲望使人变得强大,那么恐惧会让人变得脆弱,但两者都能使人变得病态、面目可憎,招来恶果。
马库斯是无神论者,罗素的门徒,在卡德威尔主任面前拍着桌子背诵《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自然不信天主教和犹太教,他理解中的死亡是,此生在死后依然困扰着逝者,通过梦境永远陪伴逝者,在一个没有钟点的世界里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对自己复述自己的故事,无休无止。死后的不确定非但不会消失,反而“由于我无法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处于什么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维持了多久,不确定性仿佛持久不息”。就像马库斯后来的室友艾尔文·艾耶斯一样,与他唯一在意的、愿意谈论的爱车拉萨尔永远地困在不确定性的云雾里,仿佛西西弗斯的永恒诅咒。在这怀疑人生的三页中,马库斯预先揭示的死亡给叙事蒙上了一层鬼魅幽灵的神秘:马库斯得知艾耶斯死亡时的呐喊“艾耶斯,我也死了!”以及当他的器官停止工作、生命真正终结时,使用的措辞是“回忆在这里停止”。
Indignation的意涵远比“愤怒”二字来得丰富,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气,而是为自己见到或遭受的慢待或不平等对待而感到震惊和激愤。马库斯当然愤怒,向转向缓慢的时代,向年过半百脆弱忽然暴露的父亲,向行为不端的室友,向突然消失的奥丽维娅,向困住生死的今生记忆,但真的能苛责其中任何一个吗?就像他脑中不断回荡国歌里,他一直好奇的那句所唱,“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每个人都是被迫的,每个人都有理由愤怒和吼叫。
Photo by Ed Leszczynskl on Unsplash